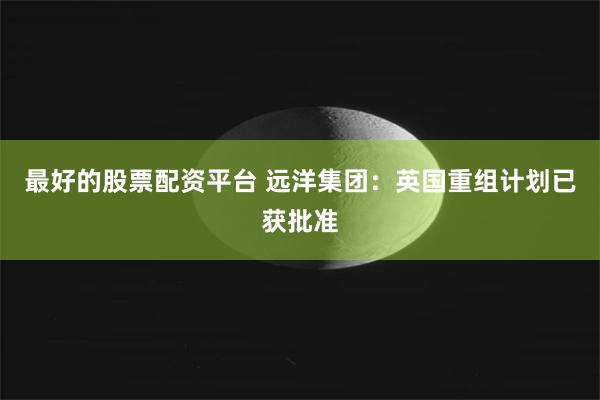兰州大学教授杨玲在其著作《先秦法家在秦汉时期的发展与流变》第一章开篇配资专业网,借助《吕氏春秋》一书的内容,揭示了那个时代治理国家的一个基本前提:个体的力量极为有限,单凭个人无法在险恶的大自然中生存,但若能汇聚成群体,就如同江河汇聚入海,便能“制服狡猾的昆虫,制伏猛禽野兽”。因此,“群体动物”这一特质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标签。在这一过程中,君主制度和君主的权威原则应运而生,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核心力量。
吕不韦则认为,国家的治理就是确立君主的地位,因此《吕氏春秋》进一步总结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这实际上为中华文明奠定了一个根深蒂固且唯一的重大命题:作为君主,如何有效统治国家。随后,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学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掀起了史称“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
儒家思想主张“为民作主”,其创始人孔子的两句经典语录深刻揭示了其核心初心。相对而言,法家思想强调“坚决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和“严刑峻法”,虽然这套理念帮助秦国从偏安小国迅速崛起为天下霸主,但法家的严酷法律和缺乏对民众关爱的统治方式也成为众人诟病的焦点。秦朝的迅速崛起与猝然崩塌,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儒家思想以“民本位”闻名,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有格”的治理方针。相比法家冷酷的刑罚和严苛的政治命令,这种以道德和礼仪教化为主的方式显得更加温和,因此赢得了历代民众的喜爱。继承孔子思想的孟子更是在“民本位”的基础上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极力强化了儒家“为民作主”的形象,把百姓的地位推到了一个看似至高无上的高度。
展开剩余75%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事实往往胜于雄辩。自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被立为国家的绝对正统,并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全面推行。此后两千多年,除唐朝短暂推崇道家之外,历代朝代对儒家正统地位几乎未曾动摇。
可是,在这漫长的2000多年里,普通百姓的地位真的高于君主了吗?在儒家倡导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理念下,老百姓的生活是否真有显著改善?不必多言,元代诗人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总结得淋漓尽致: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句话生动反映了,儒家思想中的“民贵君轻”并未真正改善百姓的生活条件或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反而使百姓沦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工具,未能享受到国家发展的实惠。
为何会出现这种反差?解答问题需回溯到创始人孔子本身。从他的两句言论中可见一斑,其对老百姓并无真正的善意,反而透露出一种利用民众、维护君权的“阴险用心”:
其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只能让百姓服从,却不能让他们获得知识和思想自由;
其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强调只有君主拥有智慧,而让百姓保持愚昧,才是治理的正道。
民国时期学者胡适曾总结,这正是封建王朝实施的愚民政策,而孔子的这些言论无疑为此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那么,当时的老百姓对孔子究竟有多大反感呢?有两个生动的例子足以让人大开眼界。
第一个例子记载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带着弟子们去卫国宣传学说,却遭到卫灵公的监视,生活毫无尊严。忍无可忍的孔子决定离开,途经卫国边境匡城时,突遭一群百姓围堵,愤怒地威胁要杀死孔子。
子路急忙问原因,百姓们叫嚷着说孔子的主张是维护奴隶主利益,而他们刚刚摆脱奴隶制的枷锁,孔子的思想等于要让他们再度受苦,若孔子不死,他们就得死。
坐在车内的孔子却异常冷静,既未出面解释,也未指示弟子应对,只默默喃喃自语:“我是周礼的继承者,只要上天不毁灭周礼,匡人是不会伤害我的。”
孔子这份从容无疑让子路等弟子既惊且忧,他们费尽力气,才勉强平息了这场危机。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孔子和弟子途经蔡国时,途中迷路。子路询问田间农夫方向时,遭到冷嘲热讽。一个农夫汗流浃背地讥笑说:“他不是很有学问吗?怎么还要来问我?”另一位农夫更是直言不讳:“他能做什么?还不如跟我们一同劳作呢。”
子路失望地回到孔子身边,却发现老师不见了。又问路边农夫,对方吐口水说:“他四肢不勤,五谷不分,还配当师傅?”
由此可见,孔子那种倾向于“愚民”和将百姓工具化的思想,令当时普通百姓心生怨恨,对他的印象普遍负面。因此,可以推断儒家所谓“为民作主”的理念并不完全可信配资专业网,未被蒙蔽的百姓对孔子怀有不少敌意,上述两个真实案例足以令人震惊,颠覆对孔子的传统认知。
发布于:天津市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联华配资_配资114查询公司_配资114提供专业可靠的查询平台观点